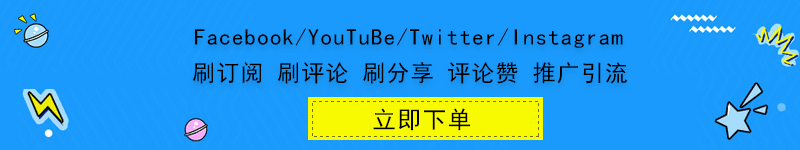摘要:从社交平台初始用户名到匿名群体的社会涌入,匿名社交迅速变成青年群体参与社交互动的隐身保护,“公共马甲”的出现代表了群体性匿名成为当代青年的一种主流匿名选择。本研究通过抓取移动数字平台中的典型社会热点事件讨论,对相应文帖进行语料数据化分析,并对虚拟空间场域进行网络民族志考察,探寻移动社交平台青年匿名社交模式的生成与表现。研究发现,由于平台带来的匿名化技术失效、社交需求满足减少及信息流动速率下降,青年选择群体性匿名即成为“公共马甲”。这样的匿名行为不仅让行动者保持了个体化的虚拟身份,同时体验了宣泄与重建功能,是青年应对社交困境的策略选择。这样的社会表现所带来的社交新世相是我国青年群体社会参与结构重建的折射,暗含青年需要更多社会观照来补足社交情感依赖。
关键词:匿名社交;身份认同;平台发生机制
在私人化空间领域逐渐锐减,公共领域不断拓宽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期望获得能保留隐私、抹去参与痕迹,从而避免“赛博裸奔”,实现“数字隐身”。青年匿名社交的社会涌入在当代社会蓬勃发展的数字化和虚拟化环境中变得尤为突出。匿名社交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社会身份束缚的平台,使青年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随着时代的演变,青年的匿名社交呈现出多层面的变迁。过去,匿名社交可能是对传统社会规范的一种逃避,为青年提供了独立思考和表达的空间。而在当代,数字化文化的崛起使匿名社交更加便捷和普遍,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个性追求、虚拟身份、社交焦虑等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着青年对匿名社交的态度和行为。而随之产生信息的不负责任传播,因为匿名性削弱了行为的社会监督也需要受到更多的关注。
自从2020年来,小红书等社交平台出现了一批使用“粉色恐龙”头像,昵称为“momo”的用户群。这些青年用户选择通过使用统一化隐名或伪名来保护个人身份,借助“公共马甲”以实现自身更自由地表达观点,避免暴露真实身份。“momo”及“粉色恐龙”作为社交平台用户注册后的初始默认用户名和头像,起初并没有获得大众的特别关注。而后部分社会性舆论事件的发酵,许多人借助这一代号实现了身份掩护,获得了表达去限制化福利,实现了群体性参与与支持。
绝大部分社交平台没有单一的中心权威机构或个体,控制或管理用户的身份信息、发言内容或互动过程,呈现了去中心化特质。采用“去中心化”的策略,让每个用户都能获得关注和话语权[1]。与传统的中心化社交平台不同,这样的平台通常不要求用户使用真实身份以实行社区管理。这种通常依赖于用户自我监督和社区监督,来防止滥用和不当行为的社区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用户“反算法推荐”的心理诉求,是一场青年人“算法驯服”的狂欢。德弗勒和洛基奇的“媒介依赖理论”认为,媒介在特定的社会中以特定的方式满足受众的需求。这样一来,媒介在受众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受众需要通过媒介平台来完成自身的表达。卡茨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将受众视为具有特定需求或动机的个体,并分析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以及媒介使什么需求得到满足[2]。基于这样的需求呈现,受众在日常生活与传统媒体的体验感降低,越来越多的青年受众选择新兴社交平台来满足自我体验需求。对于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元的年轻人来说,选择伪装自己并在自己设计的伪装下完成社会失范的实践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选择。他们摒弃工作中的认真、学习中的投入、陪伴中的专注,撕下令自己疲惫的面孔,以一种轻松、舒适、愉悦的样貌进入社交,来获取极大的自我满足。
用户沟通中的交流频次高、情感卷入程度高,形成了亲密关系则为建立了强关系[3]。个人身份的主动二次加密使得用户在不违背平台规制的基础上完成了自我隐藏,并在帖文评论互动中找到与自己想法一致的同类。这种强联系中的群体认同,能使用户拥有短暂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完成群体身份认同。在强联系下的群体匿名社交参与者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了个性化需求表现。对于个性化的表现初步可以考虑为自我选择的个性化和预先选择的个性化,一种是人们主动选择他们看到的内容(用户的主动个性化加工),另一种是算法生成的个性化内容(平台的模版个性化加工)。个体通过改变头像、拓展用户名等手段展开个性化展演,群体变得越来越庞大。这样迅速成长的青年群体对于中国网络安全及网络生活虽没有实质性威胁,但这样一群匿名社交参与者却反映了在环境急剧变化的当下青年匿名社交的诸多特征。因此,本文通过研究青年选择匿名社交的平台发生机制、行为动因及文化样貌,以期探究当代青年匿名社交的特点及其背后的青年文化。
1.青年匿名社交行为的演进
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使人们能够比在现实世界中更自由地表达自己。因此,在与他人在线互动时,有些人选择重建与物理身份部分甚至完全不同的虚拟身份。在行为人的情绪和意向表达层面,互联网匿名具有恢复、宣泄以及自我构建三个功能[4]。在泛实名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中,虽然身份匿名要求的落实无法违背互联网交流准则,但视觉匿名社交参与已经能够给予参与者极大的安全感。从本质上讲,追求利益或快乐并避免痛苦(例如风险)是人类的本性[5]。这也就是匿名社交参与的最真实成因。
互联网形态下的匿名社交经历了多阶段的演进过程,从初期的自由表达空间到后来的虚拟身份构建,再到如今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起初,匿名社交为用户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表达环境,鼓励个体在虚拟空间中探索和分享。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匿名性逐渐演化为虚拟身份的构建机制,用户通过匿名性隐藏真实身份,创造出在网络上更为自由、多元的自我形象。个体的网络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基于技术建构的。这些技术对网络用户进行数字化编码,比如性别、年龄、头像等。网络身份是自我的新身份,或者说新的自我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不同,网络身份是建构的虚拟身份[6]。但对于匿名社交来说,在建构虚拟网络身份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了部分虚假或不准确的信息。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即虚拟身份与真实身份之间的模糊边界及其所导致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的断裂。
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本质上属于人类的表达行为,而表达的内涵则远胜于传递信息,在表达的过程中人们会在语言和行为中植入意图,以建构交往的意义[7]。相较于发布的信息来说,更多的社交参与意涵旨在表达文本信息背后的价值意义和情绪表达。一项关于重建虚拟身份成因的研究对参与者在匿名社交网络社区中进行的身份重建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认为人们是出于虚荣、去抑制、享受、进入新的社交网络、逃离旧的社交网络、隐私关注和避免干扰[8]。
匿名社交给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在网络社交环节中,匿名参与者有了更多的匿名想象,这样一来匿名参与者能够将彼此想象为“某人”,而不是未知的“任何人[9]。不同的社交想象组成了群体想象面貌。同样,正如奈特所言,在群体当中,那些已经获得社会交往资格的人的共识,决定了什么样的人能够参与他们的群体交往[10]。群体认同的建构就在这样一步步的共识中建立起来。匿名社交同时也会引发多种社会问题,包括网络欺凌和虚假信息传播。匿名性让一些用户感到无拘束,更容易展现攻击性行为,导致网络欺凌加剧。此外,发布虚假信息者的身份不明确,难以进行有效监管,加剧了虚假信息在网络上的传播样态。互联网匿名社交在为用户提供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未来的发展需要在保障个体表达自由的同时,更好地平衡社会责任,推动匿名社交向更加健康和有序的方向演进。
2.平台可供性研究
作为“超级物种”的“平台”一词在学术界迅速崛起,但是至今对其并未形成共识性的定义。对其含义的讨论从实体物理建筑、经济角度、治理角度各自出发,并延伸为一种文化中介,将其视为改造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或场所,文化与意识形态生产正在平台这一“社会—技术”系统中出现[11]。因此,从文化生产与消费工作的角度出发,对平台功能性的讨论则引入了一套系统性的话语体系,此时便需要回到平台文化功能与“社会—技术”互动关系的透视之下,“平台可供性”为此提供了切入点。
可供性(affordance)由詹姆斯·吉布森提出,原指动物和环境之间的协调性[12]。在研究“新媒体”之“新”时,潘忠党将“可供性”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传媒界,此后,大量传播学领域的文章对可供性进行了讨论[13][14][15],但都集中于对可供性工具属性的强调,展现了技术对人行为的引导、限制和约束[16]。但是这背离了“可供性”一词的初衷与核心—“关系”,同文化角度的契合度较低,由此,本文对平台可供性研究的梳理集中于人与平台技术和平台环境的关系维度。
在文化研究视角下,平台可供性可以用来解释平台中的群体行为现象背后的平台发生机制。以“关系”为核心的平台可供性指向了用户的“身份建构”路径,即强调在关注技术导向作用的同时,不能够忽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简单而言,在社交媒体平台,人们会将技术的可供性转化为一种社交资源,并借助它实现对人际关系的建构[17]。并且,在平台可供性及由此产生的动态变化之下,社交网站和社交媒体超越了数字世界,悄然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技术发展所决定的,更是参与者对由可供性引发的社交参与的变化的应对策略,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一种学习在中介架构的约束和可能性之内进行自我建构与呈现的过程[18]。
综上所述,匿名社交与平台的属性密切相关,从工具属性的角度出发,平台的可供性影响了用户在不同平台上的社交行为和体验。而在文化与“关系”的维度,匿名社交与平台可供性都重叠于身份建构领域。但是目前相关议题的研究较少[19]。因此,本文从平台的可供性出发,探索群体性匿名化的平台发生机制,并解释在平台技术的变革下个体行为的变化及其背后的逻辑。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大量虚拟社区涌现,网络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网络民族志强调从“中观”层次进行分析,聚焦于具有社会集合体代表性的小群体[20]。本文研究者于2023年2月使用小红书平台进行参与式观察,以“momo”群体为对象进行田野。网络空间的田野较现实田野相比,更具多元性与流动性,若一开始便随机对“momo”群体的行为进行观察与分析,则缺少对于“momo”群体整体行为的把握。
因此,本研究设计了长达7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基本上每天都保证了2小时以上的App使用时间。在长时间观察后,研究者对“momo”群体的相关信息进行了梳理,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卷入、参与、联系、互动、分享、关系和连接,实现了与另一端的人交流[21],最终在对观察对象行为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后,依循网络民族志的技术和原则,结合本研究问题,调整研究计划,明确了本次网络调研中研究者的田野时间与空间、角色与观察对象的关系以及数据收集方法。首先,本次研究将虚拟田野场所缩小为“某主播道歉”这一社会热点事件热度前十的相关讨论帖。网络田野场所要求聚集性和可观察性,而小红书平台开放性较高,在该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即热度已下降时进入评论区进行观察,评论区域与内容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闭合性,规避了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与开放平台的不适配,符合“线上社区”的必要观察条件;其次,为最大可能保护参与者的自然环境,研究者不干扰及影响观察对象,本研究选择Python进行数据爬虫,于2023年10月收集了该事件热度前十的相关讨论帖,共获评论32432条。在剔除无效回复后(包括空白评论、广告等),有效评论数为31331条,总计字数约120万字,其中,“momo”用户发言1665条,“非momo”用户发言29666条。
匿名不仅是个体用户的自主选择,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结果。群体性匿名的发生与规模性出现的背后,指向了其所在场所的变革。个体用户加入群体性匿名,往往是对环境的一种回应。因此,应回到“公共马甲”这一现象生成的地点,以环境作为变量对其进行解释。
黑箱似的算法逻辑在社交平台如同一面镜子,时刻照应着匿名用户自身。而匿名化技术和安全加密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保护用户的身份隐私,确保其在平台上的交流不受到外界的干扰或暴露。这种技术通过采用隐私保护措施,让用户在平台上可以隐匿其真实身份。这一特征使用户能够更放心地分享自己的观点、经历和情感,而无须担心身份的暴露。但是,在匿名技术发展的同时,数字语言也在不断迭代以实现控制任务的控制社会。算法通过将“归类”的方式为用户贴上标签进行精准身份识别与标记[22],这让匿名群体更容易暴露于同质性较高的集体中。换言之,用户管理的精细化程度随着算法水平的提升而发展,用户更容易在社交平台中“显露”,由此可见,匿名技术的隐匿目标与算法推荐的显露作用之间发生冲突。
momo:“这个东西(平台)之前老把我推给熟人,被认出来真的很尴尬。”(有人对momo用户发问:“为啥叫这个(ID)”,momo用户作出回答)
平台技术间的矛盾不仅意味着用户在弱社交平台下更容易被强关系网捕捉,还强化了被“追踪”的风险。首先,匿名社交平台的成功运作离不开先进的匿名化技术,这样的匿名机制为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交互动。其次,安全加密技术在匿名社交平台的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强化数据的加密处理,平台有效规避了潜在的信息泄露和侵犯隐私的风险。这使得用户能够更放心地分享敏感信息、参与敏感话题,为年轻用户提供了一个探索多样身份的空间。在匿名平台上,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展示不同的自我,无须受到社会身份的束缚。但是由于算法入侵,匿名社交平台让数字身份与现实身份的边界更加模糊,个性化的昵称成了一种“身份证据”,让用户的可见性大大提升,可追踪的身份让持续性的网络暴力风险提升。匿名化平台仅有的匿名技术已无法通过提供一种特殊的心理安全感和共鸣体验,满足青年用户在平台社交中追求认同和理解的深刻需求。匿名机制的失效让年轻用户难以享受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社交互动。匿名社交平台为青年提供的较强的心理安全感陡然下降,在这样一个专注于发言者身份的场所,青年群体的社交压力增加,所有匿名化曾带来的福利都渐渐消逝。青年难以再次体验来自自我表露的“独特的共鸣”[23],在虚拟空间中获得与表达强认同的空间也在萎缩。社交媒体平台的新变革对青年在匿名语境下才可能寻得的社交需求满足可能正在减少。
momo:“他的粉丝很无脑......我朋友圈里前几天还给他洗白,我也只能在这种熟人看不到的地方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了。”
在匿名被算法揭开的语境下,用户发言变得局促而拘束,匿名给社交平台带来的多样性和活跃性的红利受损[24]。话题引导是信息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过去,匿名社交平台通过巧妙设计吸引人的讨论话题,引导用户积极参与互动,从而推动信息在平台上的自由流动。这种话题引导机制不仅激发了用户的参与热情,还创造了一个多样化的话题空间,使用户能够在不同领域展开深入的交流,使得信息进行双向流动。但过于精心设计的话题引导可能导致信息流向过于集中,限制了用户在多样性话题上的交流。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匿名社交平台的信息封闭样态。匿名评价机制在信息流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马甲”被“揭开”,用户反馈的机制被悄然打破,社区平台中的互动性降低,用户不再如过去般能够自由表达观点、评价他人而不必担心身份暴露。
J***不想上班:“每次都感觉你们(momo)的发言很有意思,所以就记住了。”
综上所述,算法与匿名技术的碰撞,导致用户更容易暴露于强关系之下,也面临着被追踪的可能,直接影响了用户的社交需求和平台活跃度,变革之中重塑了匿名社交平台语境。匿名社交的平台环境变革是技术与社会文化双向运动的产物,它在凝聚于个体用户的身份时,对个体用户的匿名行为实践有所影响。
没有无源头的身份,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身份,身份在原有和易变中不断被消解和重构[25]。随着网络身份匿名性逐渐减弱,并在某些场所与现实身份相混合,如此平台环境的变化落在个体身上,促使个体重新进行自我的建构。作为一个开放性平台,小红书是典型的“弱关系—弱社交”场合。但是,由于算法的发展与各种偶然事件的堆叠,个体在虚拟网络空间被现实生活中相熟识的他人识别的概率上升。可以说,在此之下,过往对网络空间固有的“陌生人间的游戏”的印象正逐步瓦解[26]。人对流变的环境的适应不是一蹴而就的,曾习惯于将网络当作社会控制真空地带的群体,在此转变下已然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开放的网络平台所面对的极有可能不是陌生人,他们要面对的还有可能是他们现实生活中不断规训他们的强弱关系网,不确定性成为普遍感受[27],虚拟空间内自我表现程度较高的用户随时面临“社会性死亡”的风险。而在个体化社会,一方面,每个人都处于被支配和监控的状态,自由被最大限度地剥夺;另一方面,又由于脱嵌性,大量的个体自由被创造出来[28]。该特征映射至网络行为中,最显著的就是网络行动者经历了“社会控制”和“自我选择”,在网络中立足一个关键性身份,进而产生了核心自我[29]。
在互联网时代,虽然实名认证已经成为社交平台的主流趋势,但匿名性依然在这个“夹缝”中存活并展现多样化的特征。在此之下,用户对一种个体对隐私的关切和对自由表达的渠道即匿名社交的需求更为强烈。用户选择加入群体匿名,实则是进行一种利用群体性身份手动匿名行为,大量自由个体虽然无法掌握技术以真正意义上摆脱被“监控”的状态,但是这一将自身“退”成陌生人的举动却为他们展开了一张安全网。从根本上来说,这样一种技术门槛较低的用户身份转变直接动力并非对治理的抵抗,而是“关系”。这种关系源自现实与虚拟,他们在“退”为一个陌生人的同时,实现了将自己“大隐隐于市”—藏身于众多陌生人,去除极具个人特色的昵称与头像,隐匿个人信息在以规避来自现实关系压力的暴露羞耻的同时坚守自身虚拟数字身份,为自己争取了充足的展示空间;同时,这也是一种对虚拟世界的关系建构的回避策略,隐匿于群体后,在无目的性的情况下,用户彼此间的可追踪性大大降低,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以轨迹重叠的方式清除痕迹。
momo:“网上好多momo,我这叫大隐隐于市。最好的匿名方式就是变成其他人。”(帖中有人对momo用户发问:“我怎么到处都能看到你?”,momo用户如此回答)
momo:“本mo躺枪啦,其实只是为了让朋友认不出自己的号。”
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方式对有匿名社交需求的青年群体的吸引并非仅有“大隐隐于市”,还因其身份给青年的个体化空间留有充足余地。在本次收集的数据中,共有1665名“momo”用户(昵称中包含“momo”即判定为“momo”用户),其中约有10%的用户选择了在“momo”的基础上进行个性化表达。此类个性化用户的昵称主要有三类:第一,点缀性的无实在意义表情符号,包括emoji中的“花”“食品”等缀饰;第二,个人状态,如“momo(减肥中)”“momo(活好每一天版)”;第三,限定词与修饰词,比如“美momo”“king of momo”等。不仅是昵称上的变动,有若干“momo”用户并未严格使用标志性的“粉色小恐龙”作为头像,在此类用户中,一类以“粉色小恐龙”头像的系列衍生图片为头像,另一类则为自由选择头像。由此可见,当代青年在进行匿名社交时并不期望以完全摒弃自身个性化为代价,他们弹性地对自己的数字虚拟群体性身份进行装扮,以实现审美追求和个体自由化展示。
在弱社交平台转向强社交的趋势下,青年选择了一种全新“大隐隐于市”的匿名方式。但是,个体选择以“公共马甲”的样貌进入平台社交的体验刺激要远高于变更匿名用户名的瞬间。匿名性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存在并不是简单的“逃避实名”的表现,而是一种文化选择和社会交往的多元体现。通过探索匿名性背后的文化逻辑,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上的用户行为和社会互动的复杂性。本研究从中观层面,整合挖掘所收集的信息,理解与再现其融入匿名社交参与群体的来龙去脉,展示一个匿名社交集合体的群体画像,考察这一去中心化群体的文化实践。
1.个体身份找寻
用户选择“公共马甲”匿名身份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过程。选择成为群体匿名成员的环节中,用户经历网络身份的演练,这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但其用词习惯会带有一定的群体性特征。对这一披上“公共马甲”的群体的语言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可以一定程度地描摹匿名社交之下的当代青年在匿名之下的模样,窥探其背后被重拾的个体身份。
(1)克制地宣泄
部分研究认为,匿名性与网络行为的有限理性有显著相关性。此类研究观点可以概述为:在于网络匿名化后人的现实资料被隐去,社会约束力大幅下降,网民容易表现出日常生活中难以实现的语言和行为,但同时,他们又会有逻辑且科学地行事[30]。群体性匿名的行为起点便是使网络社交重回匿名化状态,即这部分用户的匿名性较其他群体更佳,他们有更多的宣泄空间。该群体的行为符合已有青年匿名社交的相关定论—宣泄是匿名社交的重要功能之一,青年选择匿名社交的背后可能会不自觉地进行情绪宣泄。较之于非匿名群体,此类用户更不会试图回避冲突与迎合大众发表自身观点,如他们在评论区更少地使用了减缓面子威胁的功能的词语(如“觉得”)[31]。这侧面反映了青年在网络中不惧怕与陌生个体的矛盾产生。在个体化深入并重构着生活意义的当下,随时可能暴露于强社交关系圈的实质身份和被追踪的可能将其推向“平和”假象,但实质上,他们可能更倾向于以“张扬”的虚拟身份行走于社交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群体性匿名网络社会身份的转变结果与网络匿名化集体责任泛化、行为偏激的常识相悖,即该匿名群体的行为与其他用户相比并无明显的行为极端趋势,这反映了网络用户选择披上“公共马甲”的目的并非发表极端言论。“最佳”匿名下却未出现集体失控的狂欢,当代青年并非“垮掉的一代”—他们在现实的规训与脱轨的摇曳间,生成与创造,以群体作为藏身之处,找寻安全感与归属感。群体性匿名的功能较之于肆无忌惮地宣泄情感,更似“庇护所”。从某种意义上讲,群体性匿名之于用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支持,它过滤了实质性身份后的角色期望等结构性倦怠,让青年在其中克制却自由地实现自身探索。
(2)社交开放性的重建
网络社交本质上是陌生人社交,起点是对孤独的对抗,而当强关系所带来的自我暴露羞耻夹杂于其中,青年在网络社交平台往往呈现纠结的神情—他们在对随虚拟身份而来的自由表达空间不舍的同时,又忌惮现实身份背后的社会期望、行为规范等条条框框。而在不断的摇摆中,他们最终采取“退”为陌生人身份的策略,用投身于另一个群体的方式自我选择脱离另一个体系的社会控制。在如此抉择之中,隐匿于群体中的青年不仅更愿意与他人进行关系的连接,在对社会事件进行关注时也会倾向于对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做叙事,从“momo”便可见一斑:相较其他群体,他们较少使用“自己”作为主语,侧面反映其自我意识或自我感知减弱,在网络生活中沉浸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更小,而较多或更愿意与他人产生联系[32];同时,就LDA话题建模结果,在事件内容评价方面,“momo”群体则会倾向于以集体为主语的情绪性表达,并对事件发表更为发散的观点。
群体性身份匿名的实践底层逻辑是对自我社交的重建。规避了可能面临的“社会性死亡”风险,在“公共马甲”下开拓自我呈现空间,寻回日趋衰减的人际信任与亲密可能性[33],在隐匿的状态下通过重建社交开放性,对后现代话语体系中崩塌迷茫的“自我”进行修补,重建在社会关系中迷失的自己。
2.匿名群像呈现:青年匿名社交新世相
群体性匿名现象在社会中规模性地涌现,其背后所映射的是当今青年所凝视的社会结构。本文通过观察网络用户选择与体验“回归人群”的过程,探索用户选择该群体性匿名身份的动因及身份之下的宣泄与重建。而研究一个社会事实必须回到社会事实本身,即回到群体匿名所发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当我们用简单的“保护自我、展示自我”回答这样一群匿名化用户“大隐隐于市”的原因时,也应从功能回到结构,剖析身份的建构以更深层次地挖掘行动背后的文化含义。
(1)人与人的对抗:社交在不确定性中的徘徊
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它建立了跨越空间的社会交往,改变了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34]。在一个以科学与技术为基础的世界里,不确定性是普遍的经验[35],“无法预估”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36]。无论是身为互联网“后来者”还是“原住民”,都在经历着不确定性的打磨—前者亲身体会了互联网嵌入现实生活的巨变,而后者则需要在现实与虚拟交融的边界徘徊。“公共马甲”用户较为年轻化,基本上都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的出现实则代表了没有技术话语权的普通青年网络用户经历不确定性社交体验后的反应—网络环境常常会使他们感到无法预测未来秩序和无法控制自我,这样的经历会带给用户焦虑感等不适情绪并激发他们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动机[37]。
在传统社会,人们交往的对象一般都是“熟人”,然而社交环境发生了巨变,互联网时代,陌生人社交已日益成为主流。该社交模式的转型同时伴随着人们社会角色表演区域的扩大,原本在社交媒体中的后区已经呈现出了前区化的趋势[38]。这样的双重变革意味着人际传播话语私密性的降低与跨越地域与时域的高频次互动,进而在为个体带来社交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焦虑。而在算法迭代之间,开放性平台为每个人创造了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之间现实生活与虚拟空间交汇融合,现实中的熟络关系开始以一定概率介入陌生人社交领域。大家过往所适应的“陌生人交往”已不再安全,个体的表演剧本需要及时更新,这本质上是一种网络社交方式的变革。
现代社会中,个体决策所经历的“转换的每一个片段都倾向于变成一种认同危机”。过去依靠陌生人社交逐步构建起来的一部分自我正在瓦解,现代生存性隐喻正在遭受着存在危机[39]。而群体认同则变成了减少个体不确定性动机的有效途径,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实现了联系自我与内群体其他成员[40],在内生性地建立自尊的同时追求认知安全[41]。隐匿于群众中的青年在面对社交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时便选择了转变网络身份为集体身份的路径,即转变在在线环境中对自我的表达和探索方式,重新演绎与他人建立和变换关系,在自我呈现、自我构建、自我管理和自我变换等环节建立新的叙事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为何大众在这种外在危机带来的自我暴露羞耻面前,并未放弃虚拟空间社交?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回到格兰诺维特所提出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概念之下进行。一般而言,强关系是指一种稳定深厚的社会关系,而弱关系连接相较于强连接是一种灵活广泛的社会关系。互联网环境延伸了传统社会学意义上的强弱关系,信息的高速流动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使得每个用户扩张自己的弱关系。就延伸效率而言,虚拟空间比现实生活更具优势,这可能是个体仍选择在网络中进行弱关系的连接,没有将关系构建场所迁移至线下的缘故。而虚拟社交的不可替代性也恰好反映了一个不可否认的社会事实:时间贫困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最普遍的体验之一[42],现实生活中“低效”的社交方式已不再被需求和环境允许。
(2)人与自我的对抗:个体化自反性中的互动模式新探索
把社会成员铸造为个体,这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用户虽以集体性匿名存在于虚拟社会,但其本质上仍是以个体化的身份进行着网络互动。这种沟通模式具有同时强调“集体”与“个体”的特征—用户为避免熟人社交和消极关系的建构而隐身于群体间,这样的选择并不简单反映了自来的“面子”文化,更印证了现代社会个体化的自反性。
自反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概念简单而言可以理解为自我否定和自我革新[43]。概括而言,个体化的自反性特征为:在走向个体化的过程中,生命个体需要摆脱种种虚假共同体的统治和操纵,冲破各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羁绊和束缚。但是,一个人要成为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体,并不等于摆脱和斩断与他人的相互联系,而是应在一个更高层面和更广泛范围扩大和升华这种社会联系。
“公共马甲”群体“纠结”的网络互动模式有强烈的个体化自反性特征。他们“手动”匿名的方式摆脱了“公共生活”的“理性化”,与现实生活中按照普遍性的工具理性原则所建构而成的社会秩序挥手道别,桀骜地追求个体的突出地位;一边又投向另一个群体,不断被同化,寻求对个人身份的隐匿,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福柯的判断一致:现代人在沉浸于“个人自由”的志得意满时,实际上不自觉地已被种种理性化制度网络所支配和控制[44],个体在受动和被规训之间不断徘徊。不仅如此,以这群人为代表的青年还经历着“无根”和“无向”之间的往复。他们在选择消解现实生活中的关系以实现自我个体膨胀的时刻,意味着将个体置身于一个“祛魅”的世界中,与现代社会共同摧毁了目的论式的世界秩序,将意义的重负转移到了个体身上,而意义的寻觅对大部分个体而言都是沉重的。此时个体化带来了“无根”与“无向”。“公共马甲”成了一个隔绝现实生活的符号,在这个真空地带,个体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海德格尔对常人状态的现象学描述,甚至可能诞生为一种形似“逃避自由”的存在。
综合而言,这一群体的出现侧面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不断拉扯。他们逃避关系的人又回到了关系中,但却保持了高度的社交开放性;他们规避集体压力,但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体并日渐接受同化;他们害怕泄露隐私,却又愿意在坦言中与陌生人建立联系;他们逃离自身现实生活中已建构的既有意义,却又转向了重新表演并寻找意义的虚拟生活。而这些摇摆并非消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纠结。未成熟的社交模式正是对不断改变的社交环境的一种适应,群体性匿名涌现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青年人的拼搏:在当下不断流变的环境中,个体正在不断探寻一种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方式,以扩大和升华社会联系。群体性匿名的涌现是个体在动荡之下的自我缓冲机制,也是一个网络社交模式规模性转变的讯号。
(3)人与技术的对抗:算法社会中弱势个体的武器
马尔库塞指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揭示了文明的进步是对人进行压抑来实现的[45]。算法社会文明同样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这个判断—算法社会的不断发展加剧了普通用户的失控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失控的时代。以马尔库塞对“真实需求”和“额外需求”的区分为视角,可以看到算法社会对人进行了额外需求的强加,这是一种强制性和压抑性的标志。并且,算法社会颠覆和控制了我们的快感效应,使得只有把所有的生活捆绑在剩余快感上,个人才会获得相应的价值。在此趋势下,人可能正在走向一个单向度社会。
算法社会确立了一种算法正义的文化逻辑:算法的目的是“使自动化”,这带来了“正义自动化”的效果。换言之,这种新的科学道德下,只要算法没错,事情便是正确的;只有不符合算法的事件,才值得讨论。网络开放性平台通过算法进行“可能认识”的人推荐,并不断推送相似信息加速信息茧房的生成,在算法面前人人平等地面对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幻想,尊重算法成了算法社会无意识的律令,这本身是对人的异化。算法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精英社会,网络平台复杂的算法对普通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黑箱,他们承受着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压倒性劣势。“公共马甲”的出现象征着青年在算法社会中的抵抗力,通过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手动”拒绝算法正义文化的植入。
实际上,弱势个体在算法时代对新科技道德进行反制的行为已屡见不鲜。群体性匿名的本质是一个文化性身份,由大量重叠的层面或者诸多“次身份”构成,每个人都同时包含多种身份,这些身份相互调试,个体随着环境的变化去强调其中一种或多种身份[46]。青年选择成为群体的背后,实为通过调试其身份对算法社会适应,以“陌生人”社交重回技术造成且难以脱离的现实与网络社交的模糊地带。这是当代青年的“抗争”:个体拿起“原始武器”在算法社会中寻回自由心证权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隐隐于市”是一种弱势群体对算法社会进行软抵抗而生成的集体行动,象征着人的个体在压抑文化建构过程中的价值与尊严。
对待青年群体的移动社交平台匿名参与,我们需要给予更多的社会及学术观照。要做到对匿名社交群体的更深入关注,就需要了解该群体的准确社交表现。结合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进行学理化整合,形成了移动社交平台青年匿名社交表现模式,如图2所示。
匿名社交平台的崛起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和沟通模式,尤其在青年群体中,这种社交模式变得越来越普遍。虽然匿名社交为用户提供了一种在不透露身份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观点、情感和声音的机会,但这种模式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
首先,匿名社交平台可能导致情感问题、欺凌和恶意言论。由于用户在匿名状态下发言,他们可能更容易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攻击性或冷酷的行为,因为他们不必承担与真实身份有关的后果。这种情况对青年群体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欺凌和攻击的影响。情感问题也可能源自匿名社交中的不当言论和虚假信息,这可能损害青年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其次,青年在匿名社交中需要更好的网络素养。这包括教育和培训,以使他们具备良好的网络素养,如何辨别虚假信息、如何应对网络欺凌、如何维护自己的在线声誉等。网络素养是青年在匿名社交中保护自己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互联网信息的关键。为了帮助青年获得这些技能,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可以提供相关培训和资源,社交技能对青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匿名社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面对面的社交技能。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能更加依赖文字和表情符号来沟通,而忽视了真实社交中的非语言沟通和情感表达。青年需要支持和引导,以发展健康的社交技能,包括表达自己、倾听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等。最后,匿名社交也引发了道德和伦理问题。在匿名社交中,一些用户可能会违反道德和伦理准则,发布不当内容或参与不道德的行为。社会观照可以帮助青年明确道德原则,提醒他们不要参与不道德的行为。这种教育不仅有助于维护网络社区的道德标准,还有助于培养青年的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匿名社交在青年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但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社会观照、教育和培训在帮助青年更好地适应匿名社交环境、维护自己的权益以及保持社交和道德准则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这些支持措施,青年可以更好地利用匿名社交的优势,同时减少其潜在的负面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中心课题“线上交友软件使用的性别和代际差异”(课题编号:fnzx064-2022)的阶段性成果]
张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汤沺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周敏“.快手”:新生代农民工亚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J].中国青年研究,2019(3):18-23+28.
[2]陆亨.使用与满足:一个标签化的理论[J].国际新闻界,2011,33(2):11-18.
[3]张钧涵.弱联系的建构与强联系的削弱—抖音对青年群体社会交往的影响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9(3):5-11.
[4] Christopherson K 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lications of Anonymity in Internet Social Interactions:“On the Internet,Nobody Knows You’re a Dog”[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07,23(6):3038-3056.
[5] E. T. Higgins. Self-discrepancy Theory:What Patterns of Self-beliefs Cause People to Suffer[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1989,22:93-136.
[6]徐强.身份景观:虚实相生的数字身份及其认同[J].山东社会科学,2023(11):113-119+144.
[7]李庆林.意向的表达和阐释:人类传播的两大构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12):37-43.
[8] Chuan Hu,Li Zhao,Jiao Huang. Achieving Self-congruency ?Examining Why Individuals Reconstruct Their Virtual Identity in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Established within Social Network Platform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5,50:465-475.
[9] Sharon T,John N A. Unpacking the Secret:Anonymous Social Media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Networked Anonymity[J].NewMedia&Society,2018,20(11),4177-4194.
[10]陈曦.互联网匿名空间:涌现秩序与治理逻辑[J].重庆社会科学,2018(8):26-34+114.
[11]刘战伟,刘洁“.平台/platform”:一个概念史的溯源性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3(8):70-82.
[12] 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Boston,MA:Houghton Mif lin,1979:130,125.
[13]张志安,黄桔琳.传播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可供性研究及启示[J].新闻与写作,2020(10):87-95.
[14]陈启涵.平台可供性视角下网络对立情绪的流量政治[J].新闻界,2023(1):78-87+96.
[15]宴青,陈柯伶.可控与不可控之间:短视频成瘾的媒介可供性[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90-101+171-172.
[16]燕道成,蒋青桃.媒介可供性视角下平台数据垄断分析—超越主体—效用逻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45(12):127-136.
[17]陈瑶.微信视频号中的自我呈现与身份重构—基于平台可供性视角的分析[J].青年记者,2021(16):108-109.
[18] Boyd D. Social Network Sites as Networked Publics[C]. Affordances,Dynamics,and Implications,2010:39-58.
[19]KokilJ,AlvinZ,YphtachL,etal,Beyond Anonymity:Network Affordances,under Deindividuation,Improve Social Media DiscussionQ uality[J].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22(27):1-23.
[20][21]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M].叶伟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9,114.
[22]洪杰文,陈嵘伟.意识激发与规则想象:用户抵抗算法的战术依归和实践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29(8):38-56+126-127.
[23]马珺.匿名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传播[D].硕士学位论文,北京邮电大学,2018.
[24]王友良.网络社会要素、空间和交往过程的层级关系建构[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52(4):163-173.
[25]南长森.阅读识别身份:数字时代阅读方式变革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7(2):69-75+110.
[26]黄少华.论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J].社会科学研究,2002(4):93-97.
[2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2.
[28]张杰.通过陌生性去沟通:陌生人与移动网时代的网络身份/认同—基于“个体化社会”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6,38(1):102-119.
[29]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M].李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176.
[30]张小兵.网络表达与社会稳定[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5(3):39-44.
[31]徐晶凝.认识立场标记“我觉得”初探[J].世界汉语教学,2012,26(2):209-219.
[32]查国清,胡超然,孙铭涛,等.抑郁症网络社交与疑似抑郁微博初步筛选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2,58(1):158-164.
[33]牛更枫,鲍娜,周宗奎,等.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5):563-570..
[3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4.
[35] A lber to Melucci. Inner Time and Socia l Time in a World of Uncer taint y [J]. Time & Societ y,1998(2-3):179-191.
[36]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J].谷蕾,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11.
[37]袁光锋.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J].理论与改革,2023(3):134-143+160.
[38] Chen H L,Beaudoin C E.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Social Network Site: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J]. Telematics & Informatics,2016.
[39]潘泽泉.网络“陌生人社交”行为的心理与本质[J].人民论坛,2020(30):78-81.
[40]邓希泉.网络集群行为的主要特征及其发生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0(1):103-107.
[41]吴莹.全球危机中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极端群体认同的形成[J].社会学评论,2021,9(2):157-172.
[42]孙晓敏,杨舒婷,孔小杉,等.时间贫困内涵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稀缺理论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24,32(1):27-38..
[43]肖瑛“.反身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辨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5(2):10-17.
[44]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M].汪民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76.
[45]王雨辰.一种非压抑性文明何以可能—论马尔库塞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价值批判[J].江汉论坛,2009(10):54-59.
[46]拉里•A.萨默瓦,等.跨文化传播[M].闵惠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12-124.
提取码:5x27